来源:陆玖商业评论
如果说轮值制度是对组织权力结构的周期性扰动机制,那“人单合一”则是对价值创造链条的持续性重构逻辑。

5月7日刚刚宣布收购极氪,吉利集团的管理架构就火速迎来新的调整。5月15日,安聪慧将在吉利并购极氪完成后,出任吉利控股集团CEO,吉利控股集团首位轮值总裁戴庆,将直接向安聪慧汇报。
查询吉利控股集团官网发现,戴庆“自2025年3月起担任吉利控股集团轮值总裁”。也就是说,吉利已在今年3月开始施行轮值总裁制度。外界普遍关心,同样面临高层管理难题,吉利是否要复刻华为,推进集团核心高管的轮值制度?
对此,一位熟悉吉利汽车的业内人士向陆玖商业评论透露:“吉利和华为的高管轮值制度,有很大不同。华为轮值董事长是能做出最高决策的,但轮值期限只有半年。而吉利的轮值总裁更像是‘首席智囊’,上面还有CEO坐镇。这和华为早期的高管轮值制度相似,有轮岗练兵的味道,重点是培养高级管理人才。吉利这套‘轮值总裁+固定CEO’的组合,既能让高管有更多历练机会,也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决策分散问题。”
时至今日,华为的管理模式已经被理想、小鹏等车企效仿,但复刻华为的轮值制度还是颇具挑战,这背后,吉利集团有哪些深层次的考虑?
01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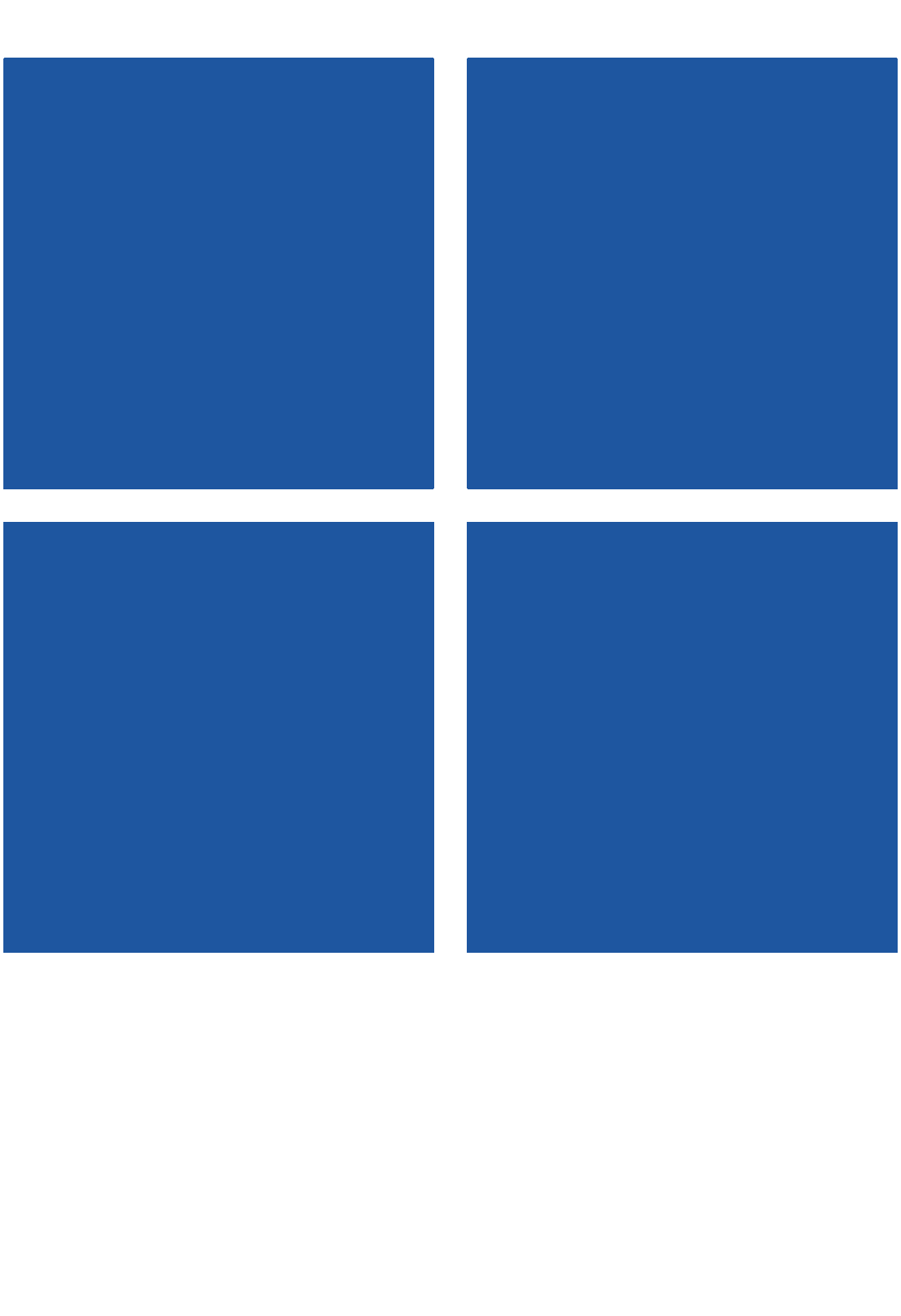
华为轮值制度的三次进化,
吉利处于哪个阶段
任何一个企业大到了一定程度,都要依靠制度而非英雄,来化解治理难度增大的问题。
时至今日,吉利控股集团旗下业务板块复杂(下设吉利汽车、沃尔沃、路特斯、吉利科技、远程新能源商用车等多个业务集团,独立结算、自负盈亏),品牌众多(业务集团下设有1个或者多个子品牌,各品牌要争取更高销量,寻求增加新品类、进入兄弟品牌市场混战),且涉及多国市场,不同业务部门、不同子品牌之间出现资源拉扯,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内耗。
进入2025年,吉利集团进一步调整阵型,梳理品牌定位,优化人事布局。其中的一大亮点就是推进高管轮值制度。但吉利的轮值总裁制度,不是简单对标华为,而是针对企业特殊发展阶段的具体问题,做出了有前瞻性的灵活安排。
多年以前,华为也面临类似问题,人员规模庞大、内部山头林立。针对这一治理难题,(2004年)华为成立高层管理机构EMT,但创始人任正非不想出任EMT的主席,而是让内部开启轮值主席制。后来,在轮值主席制的基础上,(2011年)华为推行了“轮值CEO”制度。任正非曾指出:“轮值的好处是,每个轮值者,在一段时间里,担负了公司运营官的职责,不仅要处理日常事务,而且要为高层会议准备起草文件,大大锻炼了他们。同时,他不得不削小他的屁股,否则就达不到别人对他决议的拥护。这样他就将他管辖的部门,带入了全局利益的平衡,公司的山头无意中在这几年削平了。”
后来的华为“轮值董事长”制度,主要是冲着高层决策者而来的,将职责重心从日常运营管理转向了更宏观的战略决策。为了保证创始人不丢失控制权,任正非被赋予一票否决权,就是他认为一项决策不对,就可以一票否掉。至今,任正非没有行使过一次否决权,说明制度达到了目的,在创始人还没来得及否决时,错误已得到纠正。
华为的高管轮值制度经历了三次进化:早期EMT轮值主席,主要是培养管理者的全局观;随后轮值CEO,在于打破部门壁垒、协调内部利益;如今轮值董事长,在强化全局平衡的同时,也保留了创始人对公司的掌控力。
目前看来,吉利集团的轮值总裁制度并未触及最高决策层。对此,《中国工业与信息化》总编曾纯对陆玖商业评论表示:“华为的轮值制度发展到今天,缓解了企业壮大以后的管理压力。尤其是遇见大事需要拿主意的那个人,有时就像被放在火上烤,决策者不好当。授权一群聪明的高级管理者轮值承担责任,让他们在一定的边界内对外界的变化做出判断和决策,这是华为轮值制度的精髓。相比之下,目前还不确定吉利轮值总裁权力、责任的界限在哪里,灵活性有多大?”
中国移联AI与元宇宙产业委联席秘书长叶毓睿,在跟陆玖商业评论探讨时认为:“轮值制度的最大价值,不在于形式上的更替,而在于促成企业治理权力结构的‘去中心化’与高管群体的‘全局视角重塑’。”
首任轮值总裁戴庆是一个80后,自2000年进入吉利以来,主要负责财务工作,并于2017年推动了吉利内部的财务转型。戴庆主要的贡献是让吉利的财务体系突破部门限制,大幅提升业务体系的资金使用效率。但推动吉利不断开疆拓土的,主要还是那些独立运作过品牌并主导过技术研发的人(比如CEO安聪慧),而戴庆明显还需要站在高处多一些相关历练。
02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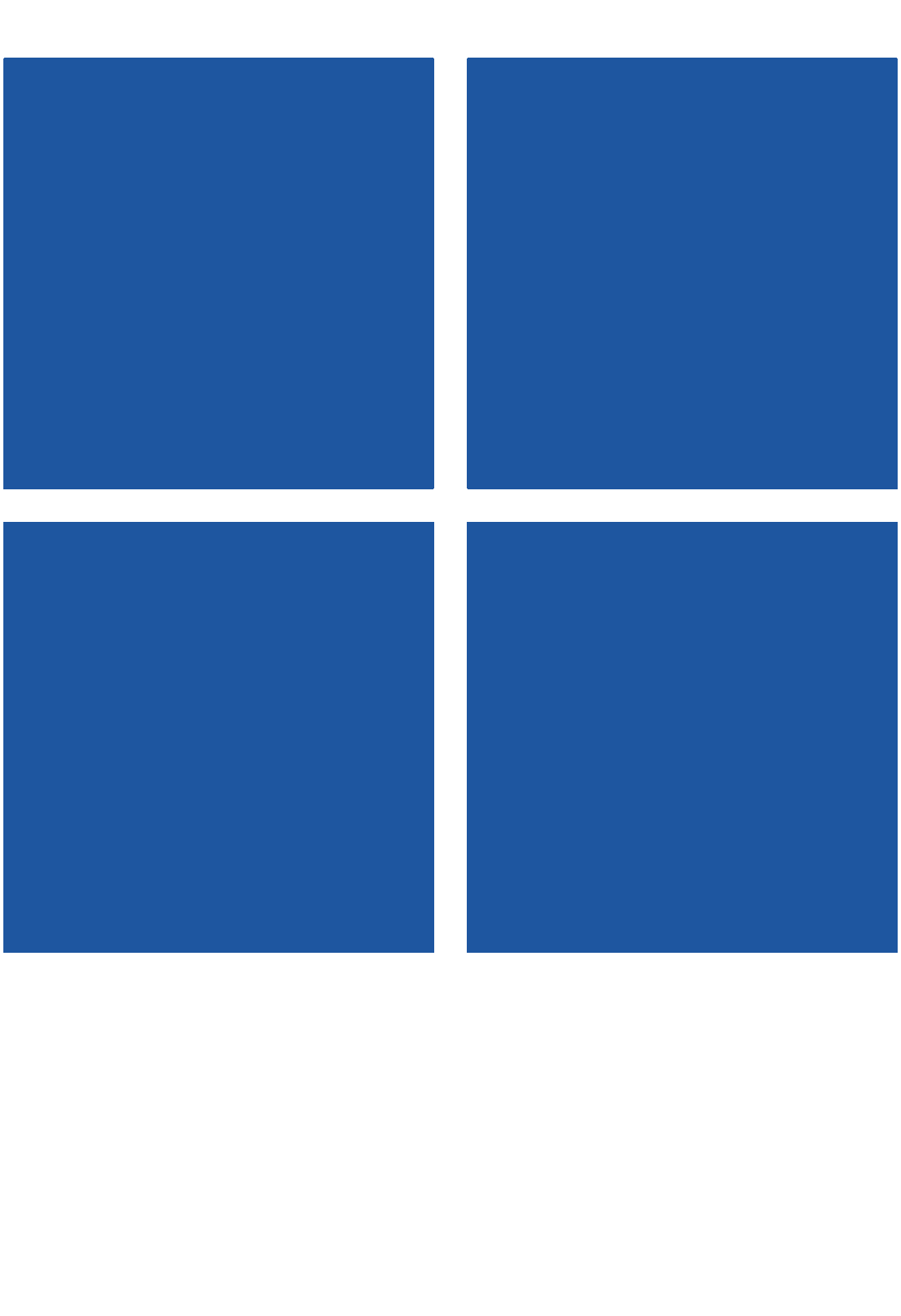
如何跳出短期得失、
局部利益的漩涡
今天,汽车产业早已开始关注并引入华为的管理经验。智能汽车的设计研发越来越复杂,涉及软硬件的大规模集成,对管理体系的要求也非常高。华为的IPD(集成产品开发)体系,擅长协调跨学科团队,提升协作效率,作为一种已被验证的高效管理模式,正契合了这一需求。
除了赛力斯因为与华为合作,在产品开发、生产及质量管理方面深度借鉴了华为模式,理想、小鹏、奇瑞和广汽等车企也跟进,将华为的组织管理策略及产品开发方案纳入自身体系。但这都只是触及肢体,而高管轮值制度则直接触及灵魂。
其实,轮值总裁制度的实行难度是非常高的。尤其是科技企业一旦面临技术路线、经营方向的重大抉择时,轮值高管怕是很难做到乾纲独断,一锤定音。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曾在第五代DM发布会上表示,曾经,插混这条技术路线已被很多车企放弃,比亚迪内部也争议不断,但自己咬牙坚持下来,继续走插混路线,走错了也认了。在当初“真的差点就走不下去了”的那一刻,还要由创始人强势拍板,不然,就不会有今天“世界最先进的插混技术在中国”。
管理层面的具体困难也不少。2018年,京东官宣启动轮值CEO制度,但这一制度并未长期延续。2020年7月,根据市场公开报道,长城汽车开始实行轮值总裁制度,两年两任轮值总裁之后,长城汽车取消了这一制度。华为、海尔的高管轮值制度运行较好,也经历了一些挫折,比如海尔就曾因为轮值交接不畅,加剧了部门摩擦,不明确职责边界与评估体系,危机难以化解,所以,有了后来海尔的标准化《轮值总裁管理制度》,以及华为的《华为基本法》。
华为董事会首席秘书江西生在一次采访中直言:“权力总量是有限的。人都有向上攀登的愿望,就算你用再巧妙的权力制衡、权力分配方案,也很容易陷入到零和博弈的困局之中。也就是说,光有否决权和轮值制度还不够。”轮值制度除了要从权力角度看问题,更要从人才培养角度看问题。
从权力角度看问题,华为从2013年就开始强调“首先要砍掉高层的手脚,接下来要砍掉高层的屁股”,就是要让决策者与部门利益脱钩。只要决策者同时兼任部门长官,就不可避免会把资源向自己的部门倾斜,导致内部利益冲突。
从人才培养角度看问题,情况就不一样了。成为高管,不再是职场的终点。轮值制度给那些聪明人提供一个站在高处看全局、看前沿的机会,当你心中有了更大的世界时,就会跳出短期得失、局部利益的漩涡。
叶毓睿认为:“轮值制度的核心逻辑,不是轮岗而是轮思,是群体共识的定期刷新。它所激活的不是职位流动,而是企业的元认知系统与前瞻机制。”
03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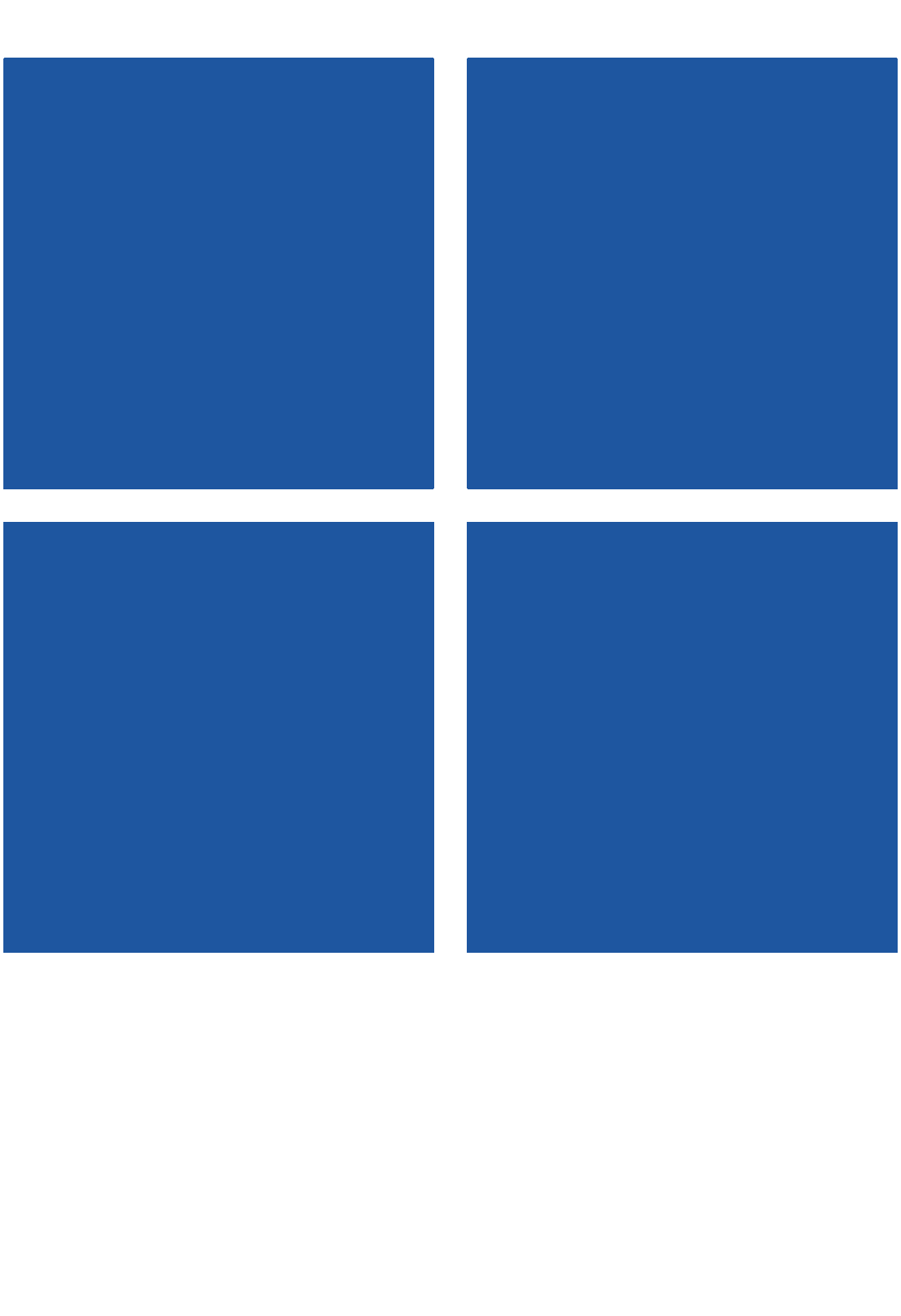
吉利可以成为汽车界的华为吗?
华为的高级管理人才都要经历一个“大循环”,比如,搞研发的管理者可能会被调去跑市场,过几年可能又被调去做销售,然后做消费者业务的大区负责人。经历过“大循环”的人,渐渐有了成为决策者的能力,也不再被部门利益困住,心中就只有华为的全局利益。
2017年,华为EMT把业务线日常经营的权力下放给部门,把制定战略决策的权力上交给董事会,之后,有了轮值董事长制度。高级管理者进一步从日常事务中解放出来,成为全公司的决策者,再用“轮值”加以约束。
华为管理顾问田涛,讲过一件小事。他有一次跟任正非喝咖啡。任正非每隔一小会儿,就要拿起手机看一眼,看着看着就说:“你看,一小时了,都没人给我打电话。前两天公司签了一单十亿的合同,我都不知道。”任正非很享受这种松弛感。
决策者时间变多了,就可以去了解各种信息,与各行各业的顶尖高手交流,吸收智慧,增强眼光,把握未来方向。
尽管吉利的轮值制度,才刚刚起步。但创始人李书福的状态,跟任正非是相似的。
为什么吉利集团具有布局未来的特殊能力?目前吉利已经拥有了30颗在轨卫星,空地一体用于智能导航;同时,成立了目前中国车企第一的算力中心——星睿智算中心2.0,综合算力达到了23.5EFLOPS;而且还能创造性地把智能座舱、智能驾驶等功能搭载于燃油车型,推动智驾层面的“油电平权”。
因为吉利的高层决策者们,已经能够较好把日常经营权下放,转而聚焦战略,经过和全球的科研天才、产业界操盘高手广泛交流,获得了捕捉未来机会的能力。
由此看来,轮值制度只是一种策略,管理层最终能达到怎样一种状态,企业最终朝哪个方向进化,需要高层管理者们根据自身情况做好调整。在这一点上,吉利在向华为学习的过程当中。
对此,叶毓睿补充道:“如果说轮值制度是对组织权力结构的周期性扰动机制,那‘人单合一’则是对价值创造链条的持续性重构逻辑。本质上,海尔的量子管理、华为和吉利的轮值制度、以及区块链DAO(分布式自组织)的去中心化实验,都是在探寻‘权力、责任、价值’的分布式新范式。它们以不同方式重申了一个时代命题:组织不再依赖英雄,而应激活系统。”















发表评论
2025-05-19 18:30:45回复
2025-05-19 19:49:29回复
2025-05-19 16:46:07回复